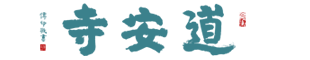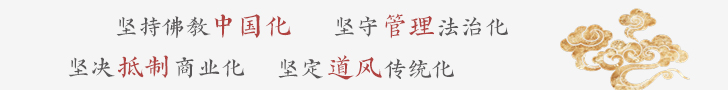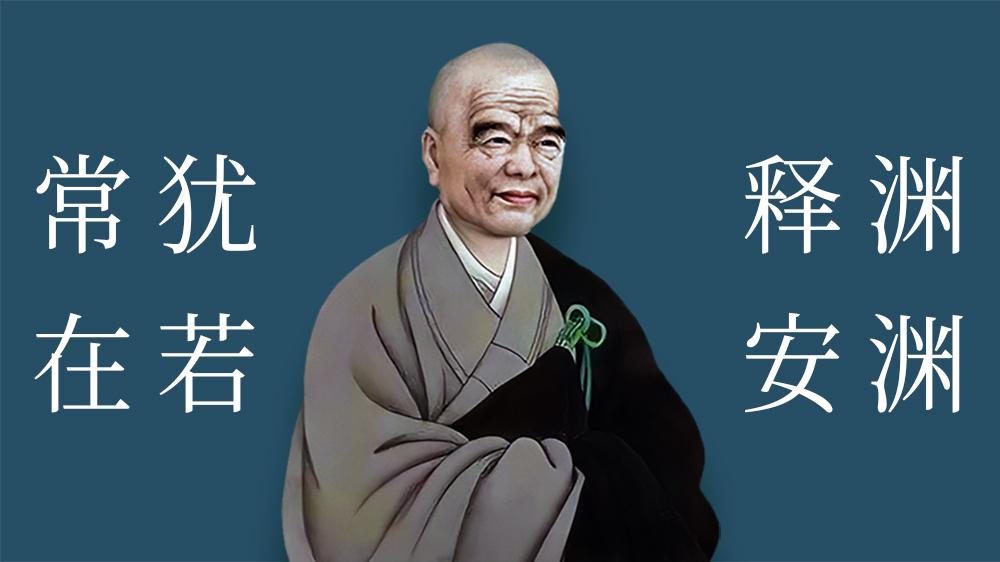道安大师对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进程中,诸多高僧大德功绩卓著,道安大师无疑是其中之一。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人,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事业,注重佛教教育的推广、普及和发展,对中国内地佛教僧团的建立和中国佛教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汤用彤称“释道安法师之德望功绩,及其在佛教上之建树,比之同时之竺法深、支道林,固精神犹若常在也。”

中国佛教的发生是以佛经的译介与推广为先导,因而在中国佛教早期发展中,佛经译介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东晋时期佛典汉译尚处于无序状态,译本质量参差不齐,辗转传抄中以讹传讹的现象非常严重。道安法师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虽因不通梵文而没有翻译佛经,但对佛教翻译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思想。
“五失本”(五种译经中的失误)涉及到译经中的语序、文质、详简、思维等问题,“三不易”(三个译经中很难做好的方面)涉及到翻译面临的时代因素、读者因素和译者因素。道安法师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如何,因资料不足,学界还有不少的争议,但他对佛经翻译上的贡献却世所公认,为当时大规模译场翻译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钱钟书先生对此评价颇高:“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释彦琮在《辩证论》中完整地引用了道安法师的“五失本、三不易”内容,认为其“详梵典之难易,铨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梁启超在论及“五失本、三不易”时指出:“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要之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
此外,道安法师还对佛典汉译的译者和译出年代严加考证,整理编撰了《综理众经目录》,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佛典目录,收录了东汉至东晋两百年间的佛典译本与注释作品,开创了佛教史和翻译史上目录学的先河,为整理佛典译本,保存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僧宝作为佛教三宝之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僧团建设成为佛教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一环。魏晋是佛教在中国社会逐渐立足并壮大的时期,佛教在与中国本土思想和文化习俗的调适中,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僧团体制,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佛图澄僧团、道安僧团、鸠摩罗什僧团、慧远僧团等。僧团的出现,有利于佛教的本土化和制度化,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道安法师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功不可没。
第一,以“释”为姓,统一中国佛门。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徒姓氏甚是纷杂,西域僧人依持本姓,如安、支、康、竺等;中国出家僧人皆依本姓,或取胡音、师姓。这一方面对中国佛教之一体化发展极为不利,另一方面,对于消弥僧团中僧众出身的阶级差别及僧团的现实差别,进而将僧团导入统一化发展也产生了很大阻碍。因此,道安法师独出心裁,以佛教“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此“遂为永式”。佛教僧尼之以“释”为姓,从而减少了由于姓氏上所表现出的国家、民族、阶级、门第差别,强化了宗教统一的色彩,对中国佛教不同地区、不同宗派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以及中国佛教僧团的统一意义非常大。
第二,为僧尼定轨范,制定中国化的僧团制度。道安僧团的内部组织管理主要依持佛制戒律。道安法师特别重视戒律,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但其时佛教戒律相当不完备,因此道安法师在佛教戒律的译传方面颇多用心。他感到僧团戒律与组织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极大地制约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意识到了完善戒律等僧团组织管理制度的迫切性。于是他一方面努力搜求与组织翻译戒律;另一方面还参照现有的并不太完备的戒律制定了中国佛教僧团的“僧尼轨范”,成为中国佛教制定中国化的寺院僧团组织管理制度的重要尝试。
第三,广布徒众,遍播佛种,为中国佛教建构信众之基石。道安法师提出了“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的名言。这既深刻地总结了外来佛教传入中土后生存的路数,又指明了佛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发展并不断壮大所要遵循的弘法新思路。道安法师“家世英儒”,尚未出家前就阅读了很多儒家文籍,他作出如此精辟的总结也是基于对中国文化及纲常伦理的了解和在佛教传入中国前所形成的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体系的认识。
总之,道安僧团在东晋时期规模极其宏大,社会评价很高。习凿齿在《致谢安书》中称赞道:“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大威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随着道安法师声名的远播,“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僧团规模随之扩大,社会影响越来越广。

在佛教义理上,道安法师对般若学做了玄学化的诠释,并依此开创“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宗。般若类经典在东汉时就己传入中国,到西晋,它借助玄学术语流行。三国时,支谦仍然沿用“本无”对译“真如”,朱士行译《放光般若经》、西晋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都沿用了格义方法,东晋之初,在士大夫阶层中更蔚然成风。佛教学者自由阐发对“空”的理解,从而形成六家七宗的不同学说。在六家七宗中,最主要有三派:一是本无说,认为无(空)为万化之始,万物之本;二是即色说,主张“即色是空”,物质现象本身就是空的;三是心无说,强调主观的心不能执着外物,外物不一定是空无的。这些学说的共同特点是以“无”解“空”,这三派正好和玄学的贵无、崇有、独化三大派很接近,即何晏、王弼等主张的“贵无”论;裴颁提出的“崇有”论;向秀、郭象提出的“独化”论,这些流派构成魏晋玄学的主要倾向。当时玄学名士与佛学名僧交往,名士以玄学谈论佛理,名僧以佛理发挥三玄,形成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思潮。
道安法师的般若学就在玄佛合流的思想背景下展开。道安法师的般若思想以“本无”为宗,以魏晋玄学的本末体用思维方式来理解般若经,他把“如”、“法身”视为根本本体,是不适合印度佛教本义的。般若经提倡空观,破除现象和本体的实有,否定本体存在,或者说主张本体是空。而道安法师则提倡“以无为本”,把破除本体实有的般若经改造为本体的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印度佛教哲学的方向,改造了印度佛教哲学的内容,构成具有中国特色佛教的本体论。昙济《六家七宗论》说道安法师是“本无宗”的代表,吉藏《中观论疏》更清楚解释道安法师的本无宗,陈慧达认为僧肇所破本无义即指道安、慧远的思想,僧肇认为道安的“本无”与方等经并论,梁武帝《大品经序》也以道安、罗什并美。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道安法师所处之时期,几近四百年。这一漫长的过程,是佛教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明相互融合的关键时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是由依附而逐渐走上独立发展之路的时期。期间,道安法师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王权与政治的关系上,道安法师以其深远卓识,提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的观点,通过佛教与政权的密切结合,依靠政权的力量,促进佛教的发展与传播。同时,在僧伽组织方面,统一姓氏为“释”,加强其内部的凝聚力;重视佛教戒律与僧团仪轨的建设,提升组织性与纪律性,为僧人提供一种有序的修持仪轨,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佛教义理方面,道安法师法师颇有其理论建树。佛教初传入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依附很大,因此无论是在佛经翻译还是在义理弘传诸层面,都深深的染上了传统思想的印记,佛教“格义”即是鲜明的代表。但是佛教“格义”在促进佛教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同时,亦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弊病,即不能正确理解佛教义理,从长远发展来看,无疑是不利的。道安法师在研究佛教义理过程中鲜明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不局限于固有师说,对此加以反对。虽终其一生未能摆脱格义的影响,但此观点之提出无疑是当头棒喝,对此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安法师之禅学,秉承其师佛图澄一系,所传为有部之禅法。道安法师之般若学理论探讨,为当时六家七宗之一,并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家,对当时盛行的般若学研究,及对般若学在中国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
(选自《第四届三禅会议论文集(上)——道安法师研究》,文章有删改。原作者为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习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