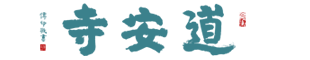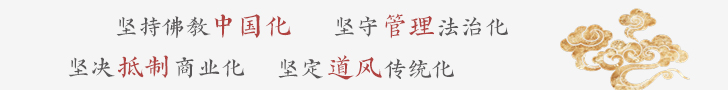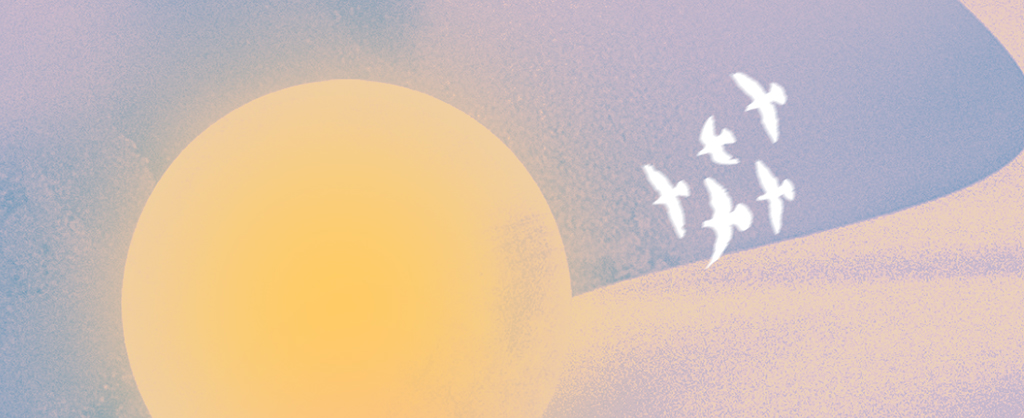善默能语 一默如雷
当西方语言哲学强调语言是与客观事物一一对应之时,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却充分看到了语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在言语之外,他更关注的是“沉默”,甚至认为沉默才是意识表达的“本体”,而语言不过是沉默的一个瞬间,相比于口若悬河与滔滔不绝,沉默反而是一种更高级、更本质、也更直接的“语言形式”,因为真理在语言尽处。
不惟如此,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古圣先贤对于“言说”与“沉默”的辩证关系有着更深刻的认识:“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大辩若讷”(《老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寓言》)、“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周易·系辞下传》)等等的记载不一而足。

昔日世尊在灵山会上,手拈金婆罗花,在大众默然,迦叶微笑之间,完成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的心传,成为禅门第一公案;而“维摩现疾、文殊问疾”更是成就了“一默如雷”的佛门佳话。

佛陀在毗耶离城庵罗树园为大众说法时,居于城中的维摩诘居士示现身疾,佛陀深知其意,先后征询舍利弗、大迦叶、须菩提等诸大弟子前往问疾,然却都言“不堪任诣彼问疾”。最后佛陀委派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率众前往探视,于是在维摩丈室内大家有了一番关于“入不二法门”真实法义的深入探讨。在文殊菩萨做了“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的总结发言后,反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以“默然无言”相对,文殊菩萨不禁赞叹“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说空说有,仍落言筌;维摩一默,声如鸣雷。宇宙的实相此刻就在维摩居士的沉默之中。

尔后禅宗大行于东土,在祖师接引学人的公案中更是常见“沉默”方法的使用,不仅有“默然”、“不语”、“良久”这类温和的形式,同时也会通过“当头棒喝”这样看起来比较极端的方式行“无言”之教。

明代冯梦龙所著《智囊》中载有一则“艺祖屈徐铉”的故事。
南唐后主李煜派遣博学多才、名著江左的徐铉来宋朝修贡,依例朝廷要差官押伴、随侍左右。但因为徐铉的学问和名望太大了,朝臣们都担心自己口才词令不及,宰辅一时也不知安排何人来应对。太祖赵匡胤见此情形,便亲自从殿前司的禁卫军中挑选了一名目不识丁的侍卫来担此任。虽然不解太祖何意,但中书也不敢再问,便匆匆催促这名侍卫前去和徐铉会和,就连侍卫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见面之后,起初徐铉口若悬河、词锋如云,众人都惊愕不已。但这名侍卫因实在无以应对,只有不发一言、唯唯诺诺点头应答而已。徐铉也摸不清这位使者的水平深浅,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高谈阔论。就这样一连好几天,这位使者和徐铉之间都没有任何的酬答应对,徐铉因此也把自己搞的很疲惫,于是也就沉默不语了。
其实当时大宋在朝的明儒硕学比比皆是,如果派他们去“角辩骋词”难道就会不如徐铉么?在该段评论中认为是“艺祖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所以采取了这样一个“以愚困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该段轶事所讲虽然不尽如“世尊拈花”、“维摩一默”那样内涵深邃,但也无妨从另一侧面对“善默即是能语”来做注脚。
无论形上形下,其实从所想到所说,便早已有了距离,言语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它的局限性。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恰如绘画里的留白、诗词中的余韵反而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更解“善默能语”真诠。